张天潘:文化交流当由非政府组织主导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天潘
作者:
日期:2012-03-11
点击次数: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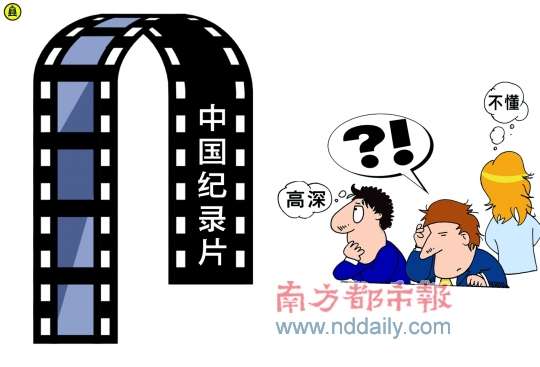
外国人称中国纪录片太高深。 李晓宜/CFP提供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 实习生卢义杰
汉斯·于尔根·吕泽布林克教授(Professor Hans-Jürgen Lüsebrink),现就任于萨尔布吕肯大学罗曼语言学与跨文化交流教研室,曾在德国和法国学习罗马研究和历史,致力于跨文化与文化多样化研究。2001年,获得加拿大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Diefenbaker奖。2000年至2002年,任德国十八世纪研究协会主席,2011年至2014年任十八世纪研究国际协会第一副主席。著有《跨文化交流的概论》、《巴士底狱:一个专制与自由的象征史》、《法语与文化全球化:政治、传媒与文学》等。
去年11月17日,吕泽布林克到中国参加了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了“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主题为“启蒙与近现代”的第四届论坛,就中西方启蒙的不同形式、启蒙及其普世价值、启蒙与民主、“启蒙”与“反启蒙”等话题和概念,与中外六位学者共同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启蒙运动不仅是一场全球性的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欧洲第一次承认世界不同文明具有多样性和深远平等性的文化运动,譬如赫尔德和狄德罗的著作。启蒙运动也强调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需持同理心和容忍度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您是德国人,本身又做过法国史等方面研究,又通晓英语等多种语言,阅历过很多国家,可谓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载体,那您曾经感受过这种跨文化之间的不适应吗?或者它给你带来哪些感触?
吕泽布林克:我确实懂一些不同的语言,我的母语是德语,此外,我懂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还稍微懂点意大利语。我对欧洲文化、南北美文化和非洲文化都很熟悉,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也有所涉猎。对我而言,接触不同的文化非常重要,能让我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全球化进程,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层面上进行不同的学习。或许因为我从小就开始接触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跨文化交流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从未有过不适应的感觉。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做好准备以面对跨文化环境,例如激发一定的好奇心,保持同理心和一定的容忍度。
南都:近年来还有一个词流行起来,叫“世界公民”。您走访过很多国家,您觉得自己算不算世界公民?在文化的立场上,您是德国公民还是世界公民?
吕泽布林克:我首先认为我是一个欧洲人,然后是一个德国公民。其实我并不十分清楚“世界公民”在今天的定义。如果它和启蒙观念里的“世界主义”是一样的意思,意味着对其他的价值和文化敞开大门,那么我就会认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南都: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样的观点在9·11,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否可以验证,当代世界的冲突确实是文明的冲突?
吕泽布林克:当代世界的很多冲突确实是文化的冲突,是基于不同价值观、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辨识模式、不同态度的文化冲突。但很明显,塞缪尔·亨廷顿低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冲突,而它们也的确是存在的。
南都:尽管人们意识到这种文化或者文明冲突,但结果却依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与相互理解,采取的对策,以美国对阿富汗战争为例,似乎有将文明的冲突进行到底的趋势。结果就是双方的误解与文化积怨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僵局,如何破解?
吕泽布林克:阿富汗的冲突和革命说明了它的文化内涵明显受到低估,美国和西方世界都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文明的冲突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文明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身份识别精神构建体系。而通过不同程度的跨文化学习,可以克服这些冲突。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案例就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冲突,德法冲突起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几场战役,而这几场战役也是由于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引起的,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开始,在亲密和平地合作中,德法之间的冲突慢慢得到了缓解和消除。
文化需具备学习其他文化的开放性
南都:德国学者有句话说,“某一个规则或某一种习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有效而是在全世界有效,那它就是全球化了的。”请问您对“文化全球化”是如何理解的?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很容易存在文化隔阂。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状态,在一些东方人眼里或发展中地区的人看来,跨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为中心”,文化成为新的渗透乃至殖民武器与方式,因此质疑文化全球化的前景,认为其将导致文化的趋同化、甚至消融民族文化。您如何看?
吕泽布林克:“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在三个层面上的全球性渗透。一是价值观念(如‘民主’和‘宽容’)的全球性渗透,这受始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极大的影响;二是广义文化产品如媒体的全球性渗透;三是某种特定文化现象的全球性渗透,包括穿衣习惯、技术产品、食物。现在对文化交流报以敌视的,基本上都是对第一种层面上发生的,即意识形态上的,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渗透,早已全球化了,在非洲的某个角落,我们都可以找到耐克、麦当劳,中国制造也是遍布全球。所以,不能就简单地把文化渗透认为是文化殖民,这样理解是很偏颇的,文化渗透不应理解为是贬义词。
南都:其实不同文化间的同化,不仅体现在欧盟各国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体现在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之间,诸如法国,也一直有对美国的“文化霸权”的担忧,于是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在这种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特殊性是否有保留的意义?
吕泽布林克:保留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特殊性非常重要。当代欧洲各国就是通过差异来保持独立身份的,这种身份的确立显然不是通过文化的同化来完成的。在1950年开始执行的欧盟政策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欧盟和北美,区分集合观念和整合观念的不同。欧盟代表了一种多种类、多语言、多文化的综合社会。该社会基于共同的机构、在人权和民主上拥有一致的共同价值观,总之,该社会的基础并不是文化的同化。
南都:那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在不同文化难以阻挡的融合之中该如何保持传统?保留与吸纳,如何达成一种平衡?哪些是需要保留,而哪些又是应该成为一种共识的、普世的核心价值?
吕泽布林克:文化应该要保卫其自有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但同时具备学习其他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并接纳其他文化中的新价值观、新产品和新技术,在此过程中并不放弃原有的语言和中心价值。这种对于其他文化“平衡的开放”是由动态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决定的,在世界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对我而言,普遍适用的价值是那些由联合国宣称的价值,比如人权、民主、男女平等、尊重不同的宗教和意见等,这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吸纳的。
价值的趋同比尊重文化习俗更重要
南都:您曾谈到“启蒙运动也强调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也说这是“欧洲第一次承认世界不同文明具有多样性和深远平等性的文化运动”。但是,这种多样性的理解,往往也发展出特殊论,从而否定或拒绝一种普世价值的发展与落实,这种文化困境,该如何处理?
吕泽布林克:启蒙运动的遗产包括,一方面是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宽容,另一方面是启蒙运动宣称了一些如“宽容”、“男女平等”、“尊重人的尊严”等普世价值,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普世价值应该比尊重具体文化习俗和价值更为重要。比如,在某些国家如阿富汗,尽管文化价值观不同,但对妇女的压迫不能容忍,同样不能容忍的是独裁或专制政权的存在,如非洲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前总统、津巴布韦现在的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曾尝试就所谓的具体“非洲价值”进行立法。
南都:众所周知,文化是深深地潜入到社会制度之中,没有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趋同,文化交流如何成为可能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社会制度的差异,才需要文化交流?
吕泽布林克:我们总是需要文化交流,这是由社会的快速发展决定的。不太进行文化交流的社会总会由于发展停滞不前或发展下降受到人们的谴责。如果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交流将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可能出现抵制文化或者反对“外国侵略”的各种运动。
南都:但这如何克服呢,或者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有,是应该先从制度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入手呢?为什么?
吕泽布林克:不管从制度上来说,还是文化上来说,都没有任何普适的解决办法。困境的解决需要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情况。一般来说,抵制活动都像伊朗一样,是由于外部镇压或者暴力统治导致的,而我们应该尽力去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很想说,如今是一个媒体全球化的时代,网络和其他媒体形式都很发达。和30年前伊朗革命时期或者150年前日本与西方完全隔绝的时期相比较,要进行激进的文化抵制或者激进地反抗“外国侵略”,远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应当注意“定性”层面的文化交流体制
南都:随着中国的崛起,尽管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文化的隔阂却已然万水千山,欧洲陆陆续续都有误解中国的案例发生,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对于中国龙的意象与想象,大相径庭,也由此对中国有了担忧,据您的了解与观察,这种担忧有无合理性?
吕泽布林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确有数不清的文化隔